因为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变化无常的,而真理则是客观的、普遍永恒的。
[25] 朱谦之:《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同一书局1928年版。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

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情感问题。情感问题之重要,连科学派也不能无视,而要认真对待。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次辩论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价值与事实、情感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由熊十力所开创的当代心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后牟宗三等人认为,儒家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而心性之学是有生命力的。究其原因,不是由于意志,而是由于情感,情便是宇宙存在的原因,……是宇宙的真生命。
由吾人之求真心与理性活动,固可使吾人有客观之神之观念,并可以论证证明神之存在。……所以‘无我,并不是于生命的流行逆而销之,而正是于生命的流行顺而达之。王夫之并不是到处都坚持这两种理的说法,但他毕竟自觉地提出了这种区分。
王夫之所说的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就是指物理而言的。体用关系就是存在及其活动的关系。有人将仁归之于情,而将义归之于知(即智),以为义就是认知理性或理性直觉,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这一点与《大学》毫无本质区别,只是将明德说成理,采用了所谓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的说法。
价值和事实可以统一,但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不同的。荀子将耳目视为天官,将心视为天君,天君具有主宰百官的作用,但心的根本职能在于知道,即认识客观之道,而要认识客观之道,还必须依靠天官提供的经验知识,必待天官之当薄其类[36]而后可。

这说明王夫之尽管对物理与性理进行了区分,但最终还是要建立以德性即道德理性为最高理性的整体综合,而不是将分析的方法坚持到底。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所以然是本然之理,属于必然性范畴。他的心统性情说就是讨论心体与情感的关系,而他的格物致知说则是讨论心体与认知的关系。
从人性的心理机能上说,仁义作为人的德性的根本标志,是由心理情感决定的。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情感 知识 。其实,仁也有这样的问题,仁的根本意义是爱,但在实行仁的过程中,也有智的直觉作用,即所谓知仁。荀子是主知的,而孟子是主情的。
而孟子则不同,他所说的心基本上是一个德性主体,作为德性主体,心首先是存在意义上的情与性,思作为心之官是从功能上说的,其职能在于使性情得以自觉,因此必须是反求诸己。但与康德的最大区别是,朱熹并没有划出本体界与现象界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是将全体和大用统一起来,即全体是用而凡用皆体。

天命就是天道、天德,不过是从天人之际上说的,也就是从人出发而说的,因此,与人的德性不能分。他在《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作中用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一点。
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名家的名辨之学,重视概念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也有认识论的意义,但这些都与情感没有什么关系。王阳明所谓格竹子之理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要求得情感上的满足,而不是求得理智上的满足。仁与义都是德性的重要内容,智才是仁与义的理性直觉。因此,知是善恶好恶之知,不是一般的知识,知善则来善,知恶则来恶,事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
命运之命,既不可改变,也不可认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前者是指自然界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规律,后者是指自然界赋予人的先天的道德理性。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妨碍知性与情性之分。
所谓健顺五常是讲天道的,健顺即《周易》乾坤二卦之性能。思不仅仅是天所给予我的思维能力,而且是有存在意义的,它就是存在之思。
问题不在于孟子是不是讲知,而在于如何讲知。孔子最重视的是仁,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分析的思维,分析的方法。至于柏拉图的理念(即理型)则是用欧氏几何学的方法进行论证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更是建立在知识论之上的,他对认识工具即逻辑学的重视,对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因此,王夫之并不否定良知良能。
德性之知不是经验知识的排列组合,其中有思的问题,但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认识,而是人生的智慧、生命的结晶,它本是人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对象认识,其核心则是知仁。如果从认识的意义上说,那么,知的范围很广,有多见、多闻之知,有知人之知,有知命、知仁之知,其中既有见闻之知,又有德性之知。
由于心(亦即情)性是天之所与我者,思也是天之所与我者,尽其心,知其性,就是运思的过程,思而尽其心,思而知其性,就能知天。人不能也无法知道他何时要死亡,寿命有多少,或何时贫贱、何时富贵之类。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与情感不可分也不能分,这是毫无疑问的。需要讨论的是,孟子究竟是如何解决知与情的关系问题的。张载对两种知即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对先秦以来关于知的学说的一种总结,而且为宋明理学关于知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王夫之的最大特点是区分了两种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两种知。他曾说过:道者,非天之道也,非地之道也,人之所以道也。
情感与认知活动都是心体之发用,都源于心体,而又回到心体,可谓之一体而异用。[43]《大学·圣经》,《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又比如他对能与所的区分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即所以发能,而能以归所,就是从主客关系、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立论的,而且是符合论的真理观。比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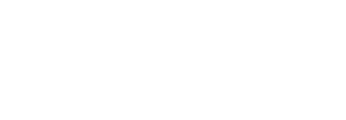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