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
(75)秦兼天下,罢侯置县,(76)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隋唐大一统王朝更是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

雍州条下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记载,孔安国传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孔颖达疏称三危为西裔之山。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也称自己的国家为天下。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8)(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20《商颂·殷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7页。在中国古代,狭义的天下用来指称王朝国家,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
(19)这也是以九州为中国的意思。这与中国古代常称四海之内九州(38)九州四海,相似如一(39)中国是九州(40)等中国为四海之内的认识相一致。它涉及对道体性质的根本理解:究竟生生是第一义,还是无生是第一义?生生是第一义,这是中华民族慧命之根。
牟宗三的新心学重视逆觉体证,冯友兰的新理学重视理智底分析(当然,这不是说牟宗三不讲理,他常说见道尊孟子,为学法荀卿。这种形上学的复兴势头可以视为在基源性与整体性上重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种自觉尝试。我非常认同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这不只是学术之争,也不只是立场之争,更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认识之争。看起来这是中西之争,实际上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七篇中就有类似的争论,即把宇宙的源头归于理性设计,抑或归于生殖、生长之争。
当今时代的儒家形上学在我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路数,一是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即通过体道的方式呈现道体,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体验型的形上学。也不是说冯友兰不讲践仁工夫,其新理学也专门讲优入圣域之门路),这两种形上学都是因应现代性的挑战而生的:在传统的道体言说中,人文化成的意义理解与自然过程的因果解释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牟宗三、冯友兰的两种形而上学中,道体的言说被分别纳入生命体验与理智分析两种不同的路径中。

对朱子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切体道,而不是凌空说道体。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丁耘的《道体学引论》与先前张祥龙、王庆节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所做的会通工作都属于形上学的建构理路,可称为天道形上学。在这两种路径之外,能不能找到第三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形上学?天道现象学是否就是第三种形上学?这或许是丁耘《道体学引论》所引向的方向?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我记得几年前,丁耘参加张祥龙新书的发布会,他提出现象学在中国有两个转向,一是天道现象学,二是心性现象学
看起来这是中西之争,实际上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七篇中就有类似的争论,即把宇宙的源头归于理性设计,抑或归于生殖、生长之争。也不是说冯友兰不讲践仁工夫,其新理学也专门讲优入圣域之门路),这两种形上学都是因应现代性的挑战而生的:在传统的道体言说中,人文化成的意义理解与自然过程的因果解释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牟宗三、冯友兰的两种形而上学中,道体的言说被分别纳入生命体验与理智分析两种不同的路径中。儒家与道家对道体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对生生是有共识的。朱子把《近思录》定位为四子之阶梯,但开卷就大谈阴阳性命之说,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难免给人不得其门而入乃至蹈虚之感,故朱子劝门人不妨从第二卷、第三卷看起,看久了再回头看道体一卷。
天道生生固然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是无目的、无主宰的。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重启道体话语?或者说我们的时代需要何种形上学?朱子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第一卷就采用了道体这个词作标题,但实际上朱子是持谨慎态度的。

我记得几年前,丁耘参加张祥龙新书的发布会,他提出现象学在中国有两个转向,一是天道现象学,二是心性现象学。它涉及对道体性质的根本理解:究竟生生是第一义,还是无生是第一义?生生是第一义,这是中华民族慧命之根。
当然我们说的目的、主宰不是西方目的论意义上的目的,也不是西方位格化意义上的主宰。无生在中国文化中不具有根源义,无和无生只具有作用义,而不具有本体义。另外,是不是要将生生接上无生?这是一个大本大根的问题。而在儒家学者中同样可以观察到形上学的重构现象,如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杨立华的一本与生生论。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丁耘的《道体学引论》与先前张祥龙、王庆节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所做的会通工作都属于形上学的建构理路,可称为天道形上学。当今时代的儒家形上学在我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路数,一是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即通过体道的方式呈现道体,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体验型的形上学。
牟宗三的新心学重视逆觉体证,冯友兰的新理学重视理智底分析(当然,这不是说牟宗三不讲理,他常说见道尊孟子,为学法荀卿。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思想中的道体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形上学存在?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重启道体话语?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何种意义上的形上学? 中国思想中的道体是何种意义上的道体?昨天吴飞通过对丁耘等学者的质疑而得出的八点结论,我是比较认同的。
我非常认同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这不只是学术之争,也不只是立场之争,更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认识之争。在这两种路径之外,能不能找到第三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形上学?天道现象学是否就是第三种形上学?这或许是丁耘《道体学引论》所引向的方向?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
儒家形上学的另一个进路以冯友兰的《新理学》(《贞元六书》之首)为代表,它将宋明理学所讲底以一种讲理的方式,亦即最哲学底哲学方式接着讲开来,所以是新理学。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里面,对董仲舒的宇宙论批评得很厉害,称其是形上学的伦理学(metaphysical ethics),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讲,只能讲moral metaphysics,只能通过一种体道的方式去讲道体。
对朱子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切体道,而不是凌空说道体。比如说《朱子语类》卷二讨论天地时,就对星辰运行、日月升降、日食月食、月中黑影乃至雪花为何是六瓣的都给出了解释,又说冰雹是山顶蜥蜴所吐,这些自然哲学固然折射出当时宋人的知识图景,但今天再讲这套涵盖自然-人生-社会的形上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形上学的复兴势头可以视为在基源性与整体性上重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种自觉尝试。不过我们看《朱子语类》开头六卷的主题也同样是理气(太极天地)、鬼神、性理,这意味着,在理学家那里,他们已经自觉地将道体、宇宙论、本体论视为整个文明的根基,它不仅为自然-人生-社会存有连续体提供了整体秩序与意义,而且也为自然现象、历史现象给出了一揽子解释方案
但是,宋明的理气形上学认为,每个物的气是共通的,其形而上层次即理在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更接近于西式的存在形上学。同时,我觉得它同我们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先性,它未必是今天哲学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在丁耘之前,中国现代哲学有形而上学体系的就是熊十力、冯友兰和牟宗三,其中熊十力和牟宗三估计不会把冯友兰列进自己的传统中,所以就等于熊十力、牟宗三、丁耘三人进入了中国现代形而上学传统,而丁耘与牟宗三挨得最近。我觉得当代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往自然及其根源的追问上努力。
前几天一位中山大学的物理学家给我看了一篇题为《暗物质与宇宙的终结》的文章,文中认为宇宙是一定会终结的,人类只是漫长的时空中的过客。因此这里有一个前后的演变。
这就意味着,用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来解释世界,两者的眼光很不一样,我觉得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但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内部,对形而上学这个传统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来。以鼎为例,最早的鼎是炊具,后来演变成礼器,今天我们则把它当成文物,三者的含义不同,但是器的材料和形状是没有变化的。宋明理学的理气形上学更接近于存在形上学,因为它要解释存在。
器物的器其实不能理解为物,因为物通常是与万物连在一起的,我们会说万物,但是不会说万器。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讲存在形上学,那么这种形上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其目的是要给世界一个统一的、持续的存在的理解,在我们已经接受自然科学的前提下,这种思路并不会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然和人的一般关系的理解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帮助,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理解人。
第一种是道器形上学,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器,这是原本的意思,它来自《易传》的说法。这一现象肯定是存在的。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也是形而上的?因为宋明理学要解释道学的问题,要把事物打通,要为所有的存在提供一个依据。第三种是宋明理学中的理气形上学。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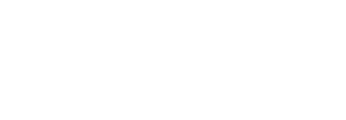

评论列表